
时间:2020-10-10 14:51:49来源:新京报
三年后,26岁的任可坐在租住的公寓里回忆起患病的那段经历,格外轻松洒脱。表达欲旺盛,滔滔不绝,眉宇眼神中几乎察觉不到愁绪,并不符合公众对一名抑郁症患者的“刻板印象”。
任可觉得自己痊愈了,并且两年没有复发。这两年,她以“所长任有病”的身份建立起了大约有6万抑郁症患者和家属的线上社群,为他们提供交流互助平台,抱团取暖,相互治愈。
“他们只是缺少被理解和被支持,当这种相信和支持从任何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得到了原谅。”
6万患者和家属的社群
在任可租住的公寓楼下的咖啡厅,记者第一次见到任可,她刚刚结束出差回到北京。眼前的任可外形优越、身形娇小、穿着入时,言谈间流露出年轻创业者的气质,让人很难与抑郁症患者联系起来。
2018年,任可创办了“抑郁研究所”,不同于以往对抑郁症的关注多以公益形式开展,任可的创业显得十分新鲜。创办“抑郁研究所”两年,她经常出现在各类比赛、创客训练营、媒体采访、新书签售会上,也认识了不少投资人。
“我最近见了好几个投资人,现在很多互联网大厂都已经关注到抑郁症赛道……”还没坐定,任可就切入“正题”。
创业圈两年的浸染让她下意识就会蹦出许多互联网“黑话”:“行业做了很多C端患者的用户教育”“我非常了解患者痛点”“供给端还不够”“要抓中间信任关系匹配”……
“抑郁研究所”在做的,就是在患者和医疗机构间搭建桥梁,患者通过专业渠道获取信息,接受有效治疗,同时对更广泛的公众进行疾病基础教育。
两年前,任可着手建立了线上社群,现在已经有约6万抑郁症患者和家属,日常用药、互助交流、线上陪伴是社群活动的主要内容。
她解锁手机,上百个微信群一时间涌入无数消息:有人“晒”出自己的诊断证明,有人展示正在吃的药物,有人咨询药物的副作用,有人纠结下次去医院取药要想什么借口向单位请假。
他们多为产后女性、留学生和年轻白领,由于切换了社会角色或是换了环境,对接触到的新信息需要一个重组和认知的过程,过往所有经验被迫改变,随之产生的适应性障碍如果没有在当下得到疏解,就可能产生焦虑或者抑郁情绪,甚至发展为病症。
她手机里还有十余个“休学群”,任可说,群里都是因为抑郁症暂时休学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少年至青年,几乎包括所有年龄段的学生,休学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一整年。
任可认为,青少年抑郁症的增长除了跟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在提高有关外,还与青少年自身紧密相关。作为互联网原住民,“00后”们的自我意识更强,线下建立的连结关系比较薄弱,孤独感比“90后”更加强烈。
她给出一组数据,在互联网上主动寻求抑郁症解决方案的人群中,18~25岁占55%,18~35岁占80%;女性与男性的比例约是6:4;南方地区占70%,一二线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比例更高。
“几乎都是年轻人。”
确诊单像一桶黑油漆
任可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有过同样的经历。
那段经历对任可来说,就像手握一块烧红的碳,无法摆脱。那时,她常常想起《梅尔罗斯》里面的一句话,“如果不能跳楼的话,要窗户有什么用”——彻底结束生命成了她每天渴求的东西,“反正没救了”。
2018年初,任可在北京安定医院拿到重度抑郁症和严重自杀倾向的诊断单时,童年那段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挨打”的经历,最终被锁定为触发抑郁症的根源。
确诊前几个月,任可睡得越来越少,每天很努力也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后来一度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以为是神经衰弱,她去医院挂了睡眠科,没想到被转诊到精神心理科。医生问了诊、开了药,但没有更多时间分给任可,后面的病人已经排起长队。
拿到确诊单时,就像被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淋了下去。
确诊后最初的三个月,是任可觉得如果再来一遍,恐怕会撑不下去的一段日子。启动性变得很差,几乎没有办法开启新一天的任何事情,呼吸、喝水、穿衣服都让她感到负累;不敢辞职,不得不包装成一个得体的成年人,努力扮演朋友圈里的自己。
“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个病治好。”和其他抑郁症患者不同的是,任可有着强烈的就诊意愿。但因为缺少必要的疾病知识,任可的依从性非常差,当药物的副作用开始侵袭她的躯体时,她坚持不住了。
她想到去做心理咨询,但医院无法提供长程的心理治疗,也不能推荐任何一家机构,医生建议她“上网搜”。她开始了漫无目的地搜寻,电话拨通,对面是痕迹明显的推销或是并不专业的情感咨询,真正能帮助她的少之又少。
“抑郁研究所”今年做过一项调查,约四成抑郁症患者和任可一样,因为相关共病或者躯体化症状,比如心悸、肠胃失调、神经性厌食贪食等才走进医院。有数据显示,我国9500万抑郁症患者确诊率仅21%左右,大部分人,包括专业医生,都缺少疾病教育,对抑郁症认知不足。
社群一位西安的患者曾跟任可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当地三甲医院看病,一位看起来经验丰富的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接待了他们。他说自己想自杀,医生告诉他,你不是抑郁症,你是巨婴症,30多岁了还每天躺在家里啃老,你现在跪下来跟妈妈认错。
那位患者走出心理科室的一瞬间就决定“放弃了”。这样的困境每天都在发生,任可说,即使患者已经有了很强的自觉,但是国内好的咨询师供给仍然非常不够,精神卫生领域的医疗仍然处在很早期的阶段,求生通道的闭塞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人放弃了求生。
无法洗刷的病耻感
严重的时候,任可也想过死,但诊断单上的“重度抑郁症”让自杀也不得不被粉饰一番。
“就是那桶黑油漆,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我不能容忍自己得了一个如此脆弱的疾病。”任可设想过,如果走在大街上有车把她撞倒,或是在出差的飞机上遭遇失事,能用这样“体面”的方式离开“就好了”。
“病耻感”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抑郁症患者和他的家庭中。
任可的父母很少将她公司的进步和获得的关注发到自己的社交圈,有时还会提醒任可,对媒体不要说生病跟家里有什么相干,就说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病友社群里,很多家属因为遗憾自己的亲人是因为抑郁症离开,出于自我保护或是为了保护离开的人,不得不去包装另外一个版本,对外称是心脏病,或者说,我的孩子出国不回来了。
活着的人仍然在努力扮演健康,每两周去复诊取抗抑郁药物的时候都要为自己的又一次请假设置一个完美的理由:上一周是痛经,下周要去拔智齿,再过两周是家里下水道漏水,也可能是我的猫要去做绝育……不能向任何人承认“我去看心理科”。
甚至在业内,也没有完全摆脱对抑郁症的偏见。任可接触过国内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专家,出于爱护,他们总是会叮嘱,“你创业就创业,不要总在外面跟人家说你得过抑郁症,这样还怎么找男朋友?”
“偏见永远都会存在”,任可认为,无法洗刷的病耻感一方面与东亚的耻感文化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抑郁症的污名化。
最近几年,一些公众人物的意外去世让更多人了解了抑郁症,抑郁症也开始逐渐去污名化。她能感觉到国内对抑郁症的关注多了起来,网抑云、丧文化、社交恐惧等也常常出现在微博超话、豆瓣小组,有人会在评论区“challenge”:你真的抑郁吗?
任可觉得这些质疑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随着信息和教育的推进,对于抑郁症的讨论变多了,社会开始去更多地关注心理健康、关注个人意识、关注群体矛盾,就像关注物质生活、关心房价、水和空气一样。
任可有一份统计数据,目前国内有9500万抑郁症患者,大约1.8亿泛抑郁人群,包括焦虑症、睡眠障碍、情绪障碍、人格障碍等。她越来越意识到,抑郁就像是情绪流感,它会传染也会流动,像感冒或者过敏一样,它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学会去接纳抑郁情绪,要防止从情绪发展成疾病。
抑郁研究所线上社群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抑郁症患者,相互治愈。受访者供图
活到好事发生那一天
创业两年,任可逐渐变成了一个有标签的人,比如“所长任有病”,就是她主动给自己贴上的标签。用这个身份,她建立社群、出书、运营社交账号、制作视频科普内容,她姣好的外形有时会引起讨论,这一切都很符合人们对一个网红的想象。
“你想红吗?”面对这样的提问,任可向后半仰了下,很快又坐直,“这对我来说不是想不想红的问题。”在任可心里,把自己推到台前,把自己的经历拿出来分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它意味着你要被审视和评判。她接受这样的代价,只要有人因为她的分享获得力量,增加求生的希望。
病友群里,任可的抑郁日记被反复转发,让病友知道有哪些出口和方式是可以尝试的。任可说,在那段绝望的日子里,是她的朋友抓住了她,构建了一个社会支持的网络,把她给兜住了。她期待,自己一手组建的病友社群能“兜住”更多的人。
回到现实,任可的公司已经拿到了第一笔投资。不同于其他抑郁症领域的NGO或是慈善基金,任可从资方拿到的每一分钱都要实现符合预期的回报。
无法逃脱的逐利本质,不能忽略的投资回报,资本希望从抑郁症患者身上得到什么?
任可坚信,资本关注抑郁症是件毫无疑问的好事,“当抑郁症形成一个赛道概念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终于能够不再以公益组织或是个人拿出全部家产,这样牺牲式的、情怀式的方法去推进产业的进步了。”
过去十数年,精神心理领域的从业者通过内容传播和用户教育,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原生家庭、亲密关系和个人成长。处在目前的阶段,任可认为应该从供给端发力,建立信任关系匹配,帮助专业的精神心理机构降低获取用户的成本,从而快速扩大规模,用更低的价格为人们提供更加普适性的服务,而不是要站到自杀边缘的时候才会启动。在这方面,资本会给予更大的助力。
对于资本与初衷之间的关系,任可更愿意看到资本向善的部分,她同时相信公司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市场和用户的行为投票,而不会全部受到资本的支配。
她认为,资本目前对抑郁症的关注还是非常冷落的,很多投资人考虑到投资回报周期而不愿涉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很难,因为它没有办法在当下给予你非常大的商业回报。”
作为一个曾经的抑郁症患者,任可经历过自我评价很低的阶段,但在创业这件事上,她不得不去做一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
她怀抱希望,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能在某一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说,你们知道吗,10年前我们还会因为抑郁症而有病耻感,很多患者甚至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事了。
“我一定要去做一个长期的创业者,陪病友们一起活到好事发生那一天。”任可说。
声明: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权、违规,可直接反馈本站,我们将会作修改或删除处理。
图文推荐
2020-10-10 13:49:56
2020-10-10 12:50:09
2020-10-10 11:51:50
2020-10-10 09:49:35
2020-10-09 19:4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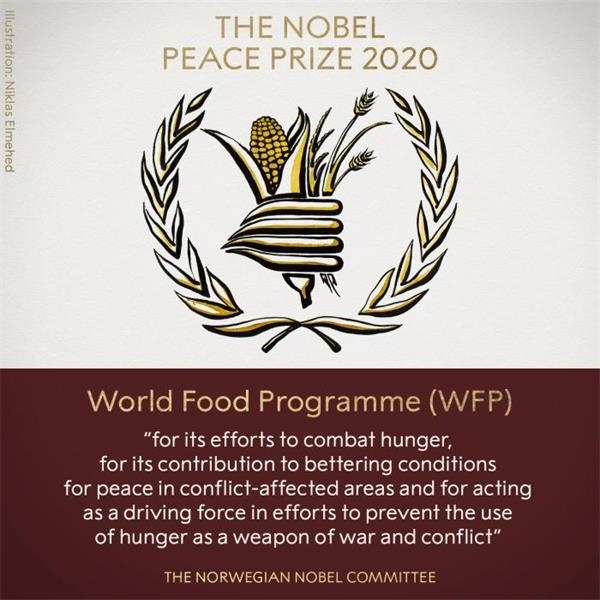
2020-10-09 17:49:43
热点排行
精彩文章
2020-10-10 13:49:26

2020-10-10 08:49:52
2020-10-09 12:51:26
2020-10-09 09:49:21
2020-10-09 08:4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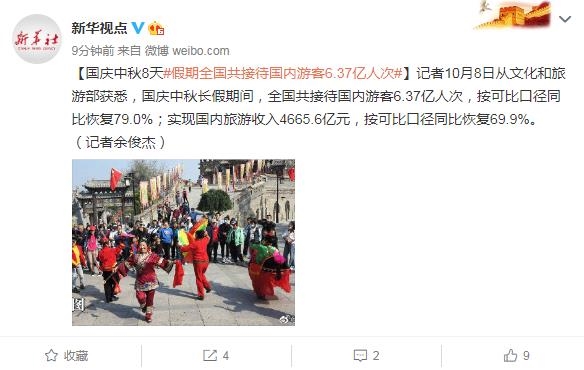
2020-10-08 18:50:10
热门推荐
